犬的記憶 | 美妙體態瑜珈在你家 - 2024年11月

犬的記憶
我選擇直接衝撞方式,揹著相機走入城市,如野犬般,浪跡在人群街道間,
而這樣衝撞的能量越是強烈,反映在作品上也就越明顯……
日本攝影大師 森山大道 首部中文版作品
80年代傳奇攝影作品「野犬三部曲」第一部《犬的記憶》
進入大師世界的首要代表性自傳書籍。
2001年日文復刻再版;2004年英文精裝出版;2009年中文版感動上市
粗樸原始、強烈黑白照片風格,赤裸記錄城市人生風景。
影像中的青春感性和活力,表現人內在強韌的生命力,
感染力道十足,深刻打動了每一位城市人。
自喻為野犬的森山大道,自八○年代陸續寫就了《犬的記憶》、《犬的時光》、《犬的記憶──終章》等野犬三部曲,被譽為是進入大師世界的代表性自傳書籍。其中尤以《犬的記憶》一書為重,1982年首次出版;2001年復刻文庫版出版至今十餘刷;2004年出版英文精裝版。
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
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森山大道
高職未畢業便離開制式教育的森山大道,強調街頭就是他的學校,靠自身學習成為攝影大家的過程令人傳誦。他以強烈黑白照片風格、擷取城市荒落一景,表現都市人孤獨冷漠但又契求與人建立聯繫的心情,感染力道十足,深刻打動了每一位城市人,被譽為是街拍大師。而他作品所呈現的青春感性和活力,表現人內在強韌的生命力,尤其受到當代日本及世界各地年輕人的喜愛及追隨。
「當我來到這個世界,邁出屬於我的人生時,其實我對於我之所以為我,還一點自信都沒有,而是逐漸才喚醒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自覺。才不久前,我的五感和第六感終於開始好好作用了,並且開始和那些促發了潛意識運作、也就是所謂的記憶的各式各樣的事物和事件產生了連繫,也讓我開始回溯這個所謂的我的個人歷史。
一九七一年我開始在青森縣拍攝流浪狗,當時我剛好從下榻的旅館走到大街上,一隻狗從我面前經過,這個機緣讓我拍下了它。從那時起,流浪狗就一直在心裡跟隨著我,這張照片讓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人們一想到我的作品,就會想到這張照片。」
──森山大道
犬的記憶,既是這張感動大多數人的照片,也是自喻為野犬的森山大道的私人回憶。書中二十篇意味深長的文章,森山分享了他的生命經歷:他生活、工作之處,家人、朋友、感情,旅行所到之處,漫走於各個城市及鄉野之中……森山在記憶之中追索,在影像之中徘徊,透過文字挖掘出在影像中交錯的記憶與真實,以及帶給他的生命意義。
這些文字完美地契合了他所拍下充滿詩意的粗顆粒黑白照片。事實上閱讀森山的文字,也能讓人感到森山內在那份強韌的生命力。不加修飾的詞藻,赤裸裸呈現森山對於城市角落的敏銳觀察,那是一份昇華自人群中的能量,正如他所說:「我選擇直接衝撞方式,揹著相機走入城市,如野犬般,浪跡在人群街道間,而這樣衝撞的能量越是強烈,反映在作品上也就越直接明顯。」
作者簡介
森山大道
1938年生於日本大阪,原只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平面設計師,在照相館中偶然見到威廉.克萊因的成名大作《紐約紐約》,受到極大啟發;1961年決定轉赴東京,投靠細江英公門下從助理做起。三年後獨立發展。
1968年首次出版攝影集《日本劇場寫真帖》,顯現藝術家風格的強烈印記;1969年在《Provoke》雜誌嶄露頭角,以模糊、晃動、高反差、粗粒子,成為森山風格的明顯標記,並在日本廣告界形成一股狂熱模仿風潮。
70年代森山歷經自己生命中的整理期。作品風格轉而呈現失意、絕望,抑鬱黑色,就連盛放的櫻花,在森山的鏡頭下也變得晦暗淍零。甚至被評論家推測有自殺傾向。為擺脫陰霾,森山受日本設計大師橫尾忠則之邀,遠赴紐約,游移在異國城市之中。
80年代,森山逐漸擺脫低迷,《光與影》(此一傳奇絕版品已由講談社於2009年4月重新出版)的出版,表現森山昂首直視景物的鮮明意志,使日本評論家驚艷不已。媒體並以斗大標題報導:「森山大道終於回來了!」
90年代起,頻繁於日本海內外舉辦主題個展及大型回顧展,1999年舊金山當代藝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美國各城市巡迴展;2002年倫敦及紐約個展、2003法國卡地亞基金會大型回顧展;2004至2009年陸續在科隆、阿姆斯特丹、奧斯陸等城市受邀個展;在日本,單是近一年內,即已舉辦了近十場展覽。
攝影集及文集陸續出版了數十本,包括《遠野物語》、《新宿》、《大阪》、《寫真對話集》、《凶區》、《另一個國度》、《森山。新宿。荒木》等。近年在日本一年約出版2-3本作品(包括再版)。
譯者簡介
廖慧淑
東京外語專門學校日中翻譯科畢業,並於視丘攝影學院研修攝影。曾任《遠見》、《卓越》雜誌記者;《WA.SA.BI.日本四季之旅》、《AZ時尚旅遊》雜誌採訪編輯、日文編譯及攝影。目前為自由工作者,專職翻譯及攝影,譯作有《巴黎.家的私設計》、《這是一場從巴黎地鐵開始的小旅行》;攝影作品主要為音樂CD封面攝影、演唱會攝影及雜誌攝影。
第1部 犬的記憶
陽光普照之處
停擺的時間
在路上
地圖
夜終究再來
另一個國度
八月之旅
陰暗的畫
夢中之街
再會
時間的化石
城
海邊的日記
鏽蝕的風景
光的神話
第2部 我的寫真記
攝影 你好
相逢有樂町
穿梭街頭
攝影 再見
於是 光與影
導讀
關於森山大道∕文.沈昭良
「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森山大道
數十年來,一直以鮮明獨特的影像表現、強烈的民族風格、近乎苦行式的拍攝方式,遊走於世界各地城市;勇於開創的恣意與銳氣,即時回應時代與城市變遷,反覆梳理攝影與自我、時代、環境間關聯,影響諸多攝影創作者,而作品形式風格足以獨立成為攝影敘事論述,乃至曾於全球主要城市美術館舉行回顧展的攝影家,首推來自日本的森山大道絕不為過。
一九九九年,美國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為森山大道舉辦了名為《彷徨之犬》的大型巡迴回顧展,森山攝影作品中那強烈而獨特的影像風格,廣受美國藝術界與媒體的普遍肯定。《美國藝術》甚至稱他是日本首位在美國一流藝術博物館舉辦完整回顧展的藝術家。《彷徨之犬》接著更巡展至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日本協會畫廊。其後於二○○三年,法國卡地亞基金會同樣為他在巴黎舉辦大型回顧展。二○○八年,日本東京都攝影美術館為這位揚名全球的本國攝影家同時舉辦《夏威夷》個展及回顧展,同時出版關於森山大道作品的論文集。今年(二○○九)六月起至明年(二○一○年)三月止,森山更將伴循著記憶,史無前例地於北海道的札幌、夕張、美唄、東川町等地,大規模巡展北海道系列作品。
回顧森山在本書中,所陸續提及的幾個關鍵轉折和發展脈絡,森山可說在辭去細江英公的助理工作後,正式開啟他近乎壯遊式的,無悔開闊的攝影旅程。一九六九年三月,森山更在由中平卓馬、高梨豐等人發起的《挑釁》(Provoke)雜誌中嶄露頭角,模糊、晃動、脫焦、高反差和粗粒子,頓時成為森山作品風格的明顯標記,直接影響當時許多對攝影的形式與內容懷抱疑問的年輕攝影者。其後雖曾引發日本廣告業界一股令人尷尬的爭相模仿風潮,但森山已然在眾多追隨模仿者間,奠定其屹立不搖的根基。
綜觀森山大道的創作歷程,一九六八年集結出版的《日本劇場寫真帖》著實為森山烙下具作家風格的強力印記,惟七○年代的森山作品,普遍呈現失意、絕望和悲傷的抑鬱黑調。就連春暖和煦白花盛放的櫻花樹,不僅是在晦暗中綻放,枝葉也彷若乾枯血管般蔓延凋萎。長期關注森山作品的日本評論家,甚至懷疑森山是否會走上自殺一途。森山為擺脫這樣的陰霾,在整理完《攝影 再見》與《狩人》的出版原稿後,旋即遠赴紐約短暫停留,期間,除了歷訪藝術展館,森山游移在曼哈頓街頭的步履依舊晦澀沉重。
森山創作歷程中的另一個關鍵性壯遊,則是當《日本劇場寫真帖續集》(一九七八年)出版後,延續類似上述的質疑與探問,這次他選擇了北海道。
一九七八年晚春至初夏(五至七月),森山在友人的協助下,在位於札幌東部郊區的白石區租了一間公寓,開始他為期三個月的北海道行旅。由於是短期停留,森山只準備了一張小桌子和顯影底片所需的工具,同時以此處為基地,放射狀地往返於函館、小樽、旭川、萌留和網走等地。外出之餘,森山除了書寫攝影日誌與閱讀,陪伴他的幾乎就是失眠、長夜、低溫、土司和威士忌。
至於為何選擇遠赴北海道,除了森山希望藉由拍攝行為,檢視與驗證自我做為專業攝影家的意志與職能之外,尚含括森山深受明治初年,也是日本攝影發展黎明階段,由田本研造所攝之北海道作品的影響。由於這些攝影作品的拍攝動機,雖以調查、記錄和測量為主要目的,惟傑出的美學實踐,看在森山眼裡,實已超越攝影的資料性與記錄性意義。加上孩提時期的森山,即對津輕海峽那頭的北海道風情,懷抱著如異國般的嚮往,以及森山試圖讓自己身處在另一個陌生的環境,擺脫當時如同行屍走肉般的生活內容與氛圍等等複雜的緣由。
而這批迄今三十二年的珍貴底片,在森山緊接著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創作後,並未能及時發表,也就這麼默默地在角落裡沉睡了三十餘年。直到二○○八年十二月,位於東京的Rat Hole Gallery為森山大道策劃了名為「北海道」的個展,這批作品才得以完整面貌公諸於世。
一九七○年代後半對森山大道而言,那段持續質疑,四處尋找自我與攝影關聯的蕭瑟歲月,從《攝影 再見》及《北海道》系列中,那股分別隱藏在抽象與具象之間,莫名漂浮的焦躁與無力感,對照現在的成熟穩健,應是既痛苦卻又甘醇甜美。綜覽《北海道》中諸如津輕海峽上的迷濛與浪濤,札幌市街的俯視擁塞,雜杳寂寥的市集,無亙綿延的濕原景緻,呼嘯疾駛的列車,車廂內濕黏的霧氣,女子青澀的回眸凝視……隱約望見那逐漸沒入荒原的纖瘦身影,拖行著探尋未知的步履,消逝在三十二年前的寒夜、北國。
直到一九八○年代,森山在精神上才逐漸擺脫低迷渾沌,《光與影》的付梓,更是重現森山昂首直視景物的鮮明意志,驚艷不已的日本評論家,甚至以斗大的標題宣示「森山大道終於回來了」。延續上述的脈絡,不難發現森山數十年來不同時期的作品中,緊密且及時回應他自身的生理與思想狀態。二○○九年四、五月間,為配合《光與影》攝影集的復刻發行,位於東京的BLD藝廊,重新推出「光與影」系列。由於展出內容與設計,獲得高度的評價與迴響,主辦單位甚至像演唱會般,以「安可」之名將展期延長了兩週。
至於其他各時期取材於城市街頭,諸如《日本劇場寫真帖》、《紐約》、《巴黎》、《布宜諾斯艾莉斯》、《新宿》、《東京》、《上海》、《夏威夷》等膾炙人口的攝影專題,也絕非只是即興式的街頭抓拍,而是含括森山與當下城市中的建築、景觀、人文、流行、氛圍等等對話的影像濃縮,內化後再藉由視覺形式所進行的深刻描寫。
二○○八年三月初,森山大道旋風式短暫停留台灣,謙卑有禮的應對,令所有接觸過他的人印象深刻。當然對這位才華洋溢、影像嗅覺敏銳,自喻為野犬般的街頭攝影家而言,寶島台灣自然是不可錯過的拍攝題材。他不免俗地登上台北一○一大樓的展望台,鳥瞰這個既陌生卻又似曾相識的國度與城市,隨即馬不停蹄地遊走在西門町、萬華、大稻埕、永康商圈的街頭巷弄間。其間,他不假思索地舉起相機鎖定、游移,狂躁如入無人之境。唯獨在龍山寺,森山如同台灣信眾一般,高舉整齊擺盤的玉蘭花虔誠禮佛,為即將走入禮堂的女兒祈福,桀敖灑脫的浪子,頓時化為深情款款的慈父。
夜晚,則落腳在師大夜市附近的一處小咖啡館,那裡的內部陳設氛圍,近似陪伴他大半歲月的新宿黃金街酒吧商圈,更令他顯得輕鬆自在。混雜著裊裊炊煙與咖啡香氣,勾串著他的過往與追憶。直到午夜時分,野犬的身影,才兀自游移消逝在黝黯巷弄深處。
後記
我正在為《犬的記憶》寫後記,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版散文集。至今雖然讀過很多其他人的後記,一旦輪到自己寫,沒想到寫後記是這麼令人高興,卻又害羞的事。當然,這本文集本身也是如此。一想到自己貧薄的想法、思考、言語,以及經驗,成為活字出現在更多人的眼前,我感到難為情很想消失。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帶些誇耀的感覺。《犬的記憶》從八二年的四月開始,到八三年的六月,十五個月的時間,連載收錄於《朝日相機》,之後加入新寫的「我的寫真記」,算是對我個人攝影的半自傳經歷。關於內容,反省、曖昧,無法停止的部分,現在再多說什麼,聽起來都像是藉口,我就不多說了。
八一年的秋天,到八三年秋天前為止,在有樂町咖啡店,經常與《朝日相機》編輯部的丹野清和見面,使得《犬的記憶》連載計畫啟動。丹野先生當時身體不好,我對相關照片常缺乏真摯的處理態度,為了將連載具體化,經常將我從攝影現場帶回來,為我創造新的挑戰契機。此外,在幾次攝影旅行中,一起同行,用實際行動激勵我,為我創造愉快的旅行經驗,我永遠不會忘記。對我來說,經歷十五個月,通往記憶的旅程,經常也是通往新記憶的出發點。光=記憶=照片=歷史=自己,無限的循環與嘗試錯誤。我以《犬的記憶》作為跳板開始,藉由記錄光線的照片通往記憶的旅程。
與這本書糾纏許久,終於結束後,現在我卻深切感慨。當時不顧一切生存,反而只留下淡淡的實感。一九六○年代後半數年間,一直到一九七○年到達頂點。那個時代的許多記憶,對我來說,我就像是不斷追尋從我手中逃走「悲哀的鳥」一樣,感到遺憾。或許這只是情緒上的感傷,看在我這麼愛惜身處的時代的份上,或許我已經可以瞑目了。
一個記憶喚醒另一個記憶,之後再探尋新的記憶,時間循環不止。今後我擁有的記憶,究竟是什麼樣的記憶呢?
※犬的記憶──陽光普照之處我的哥哥名字叫做一道,虛歲二歲時離開人世。我跟哥哥是雙胞胎,當然我沒有任何關於哥哥的記憶,若說哥哥是森山家的翻版,那我就是哥哥的再翻版。因為我的名字是大道,是在哥哥名字的「一」字中,插入一個「人」,所以我存活下來了。昭和十三年十月十日,接近中午的時刻,我們誕生於大阪府下池田町宇保(現在的池田市宇保町)的一家職工宿舍。根據母親的記憶,那天風和日麗。當時父親在一家總公司位於大阪的壽險公司上班。我們的出生地宇保位於郊外,周邊有很多樹木,屬於悽涼的住宅區,整天都會聽到某處傳來阪急電鐵寶塚線的鳴笛聲。照理說我應該記不起當時的事,但不知為何,在我腦海中總是浮現某些影像。或許不該說那是既視感,因為在陽光普照的風景中,朦朧的影像總是不斷出現,很像是浮現在虛幻天空裡的蜃氣樓。那年冬天,我們一家因為父親工作轉調,移居到廣島。聽說那時候我的身體好像非常虛弱,為了養生,雙親將我帶回故鄉托付給祖父母。祖父家位於島根縣的石見地方,是一處面向日本海的小村莊。我在那個海邊的村莊日漸懂事了。那麼,偶爾浮現在眼前,如幻影般的光景,究竟從何處被喚醒呢?池田町,現在的池田市,位於大阪平原的西北方。猪名川流經城鎮的盡頭,與兵庫縣西川市相連。從古時開始就是具有歷史的地方,比灘更早成為釀酒之地,因此池田也被稱為北攝的要衝。現今則是商業都市大阪的衛星城市,也殘留許多古時的商家及倉庫,既熱鬧又清靜。雖然我在這裡沒有幼兒時期的記憶,也沒有在某處與某人的共同記憶,然而不知為何,這裡卻令人懷念。緣因於此,在《朝日相機》雜誌第一回連載的「犬的記憶」專欄,我無論如何都想以此地為開端。這裡不是我出生後成長的地方,也不是我的故鄉,更不用說也不熟悉。雖說有影像出現,但畢竟只是幻影。在我心中只留下「宇保」這個地名。然而在我記憶深處,朦朧輪廓、陽光普照之處,卻總是縈繞於心。我並非想要追尋失去的時光。若我對池田這個地方沒有絲毫感傷的話,就無法產生望鄉之念。若無足以對照的過去,也無法將心情寄託於幻想,更不用說能夠對著幻影按下快門。更侈言,將過去與現在、或是將現在與過去重疊在一起檢驗記憶。本來所謂的記憶,就是呈現自己內心懷念的心情,而非再現個人的影像,以現在作為分水嶺,連結距離遙遠的時間點,跨越心中的領域。我能做的,僅有暫且先回到池田這個地方,將鏡頭面對著眼前的光景。這麼一來,突然傳至指尖的知覺,或許能夠喚醒記憶。懷著這樣的期待,我帶著相機,前往我的出生之地。今年(一九八二年),一月中旬的某個週末,我在東京車站搭上「光號」(Hikari)。那天天氣晴朗,但午後非常寒冷。富士山看起來異常地美麗,前往大阪的電車裡,我逕自望向窗外,不可思議地,數十年後再度探訪的出生地,我卻沒有任何一點感慨,只是茫然地抽著菸。傍晚時刻,電車抵達大阪,我緊接著從人潮擁擠的阪急梅田站,轉乘寶塚線,十三、曾根、岡町、豐中等,令人懷念的站名逐漸出現,傷感也漸漸浮上心頭。不知是不是因為是週六的晚上,池田車站黑色人影熙熙攘攘。因感傷而濕潤的眼裡映現著街燈。我就像是一位旅人,探訪一處從未前往的地方,心情上也像是在測量遠近一樣,徘徊於時間與空間之中。我把相機背在肩上,重新收拾心情,姑且先朝著寒空中凝固不動星星的所在地前進。結果,那天夜晚,我就像是蟲一樣,從這個燈飛往下一個燈,只在車站周邊閒晃。因為天氣寒冷和多少有點疲累,想找個地方休息,我沒有拍下半張照片,為求溫暖,我很早就進入一家咖啡店休息。店裡的熱咖啡很好喝,我透過因暖氣而起霧的玻璃窗,觀望窗外忙碌的人們與車子,總算鬆了口氣,回到我自己。我想要探尋的記憶,對我來說,究竟是什麼呢?這才開始漫無邊際地思考了起來。
 不一樣的對症調理飲食&養生調息運動
不一樣的對症調理飲食&養生調息運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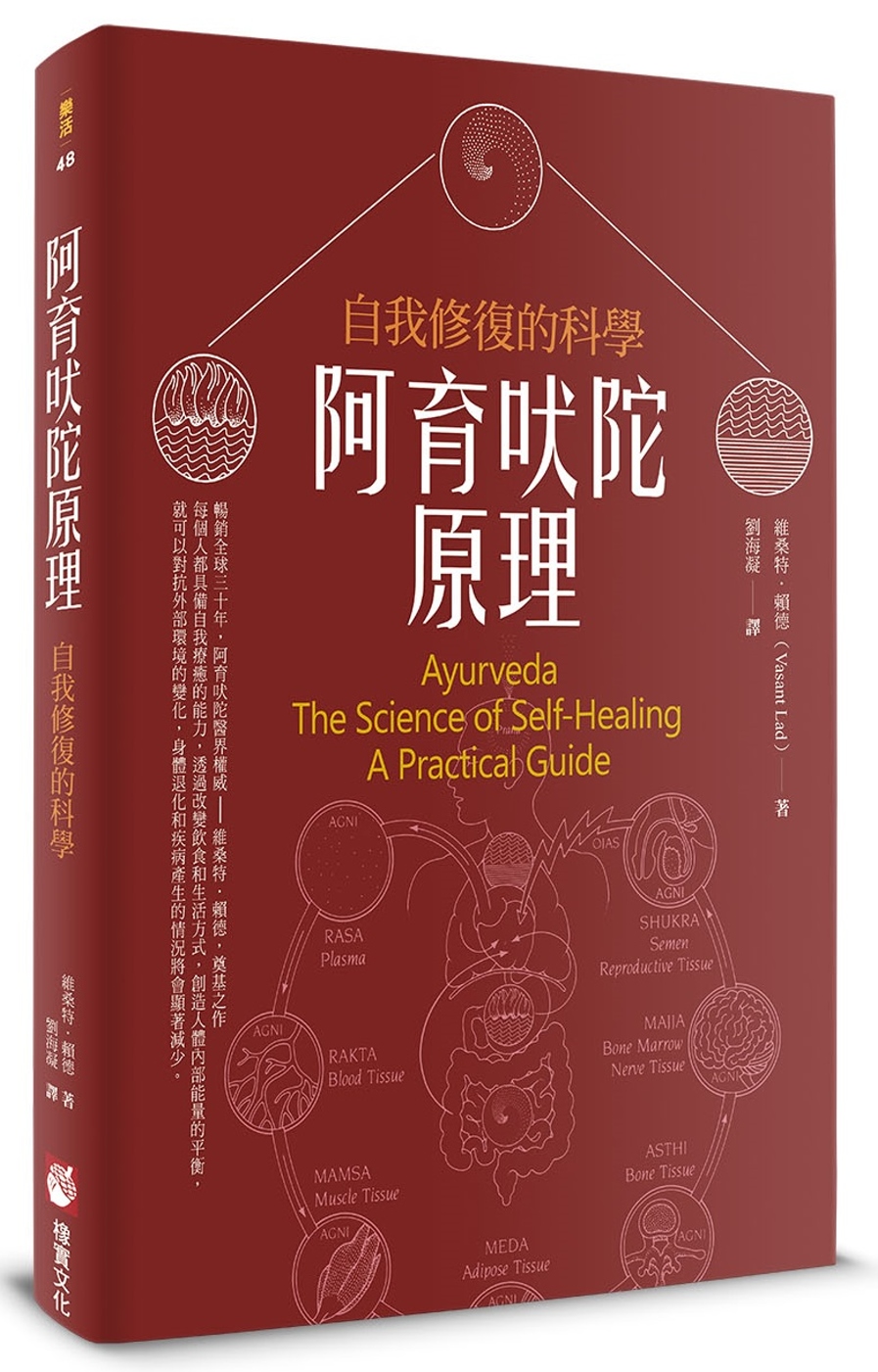 阿育吠陀原理:自我修復的科學
阿育吠陀原理:自我修復的科學 30天解決肩頸腰背痛:神奇的瑜伽療...
30天解決肩頸腰背痛:神奇的瑜伽療... 肌膚也需要放輕鬆 ─徜徉天然風的4...
肌膚也需要放輕鬆 ─徜徉天然風的4... 來去寺廟住一晚:超省錢!美食、美景...
來去寺廟住一晚:超省錢!美食、美景... 上帝永恆的愛
上帝永恆的愛 根本:元然理天王教你從後天修回先天...
根本:元然理天王教你從後天修回先天... 內在的微笑:引導式冥想(書+中英文...
內在的微笑:引導式冥想(書+中英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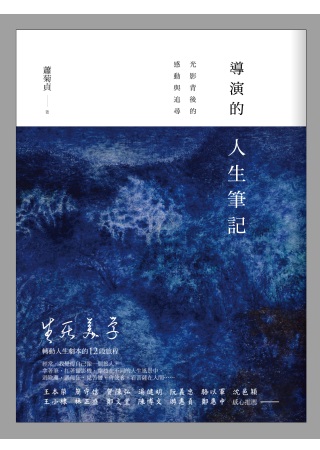 導演的人生筆記:光影背後的感動與追尋
導演的人生筆記:光影背後的感動與追尋 靈氣的世界
靈氣的世界